最近有个新闻挺有意思:中国驱赶《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没收这些媒体记者年底前到期的记者证。
外交部的表态是,这是对川普政府对中国“大外宣”限制举措进行的报复。
外交部说,这是正当防卫。美国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严重损害中国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严重影响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正常运作,严重干扰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它要求美国方面改弦更张、纠正错误,并威胁美国不得一意孤行、错上加错。
其实,中国的报复行动早在今年2月就开始了。它当时吊销了《华尔街日报》3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和签证,理由是:《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辱华文章。
《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是美国保守派外交学者米德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评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标题据说叫做《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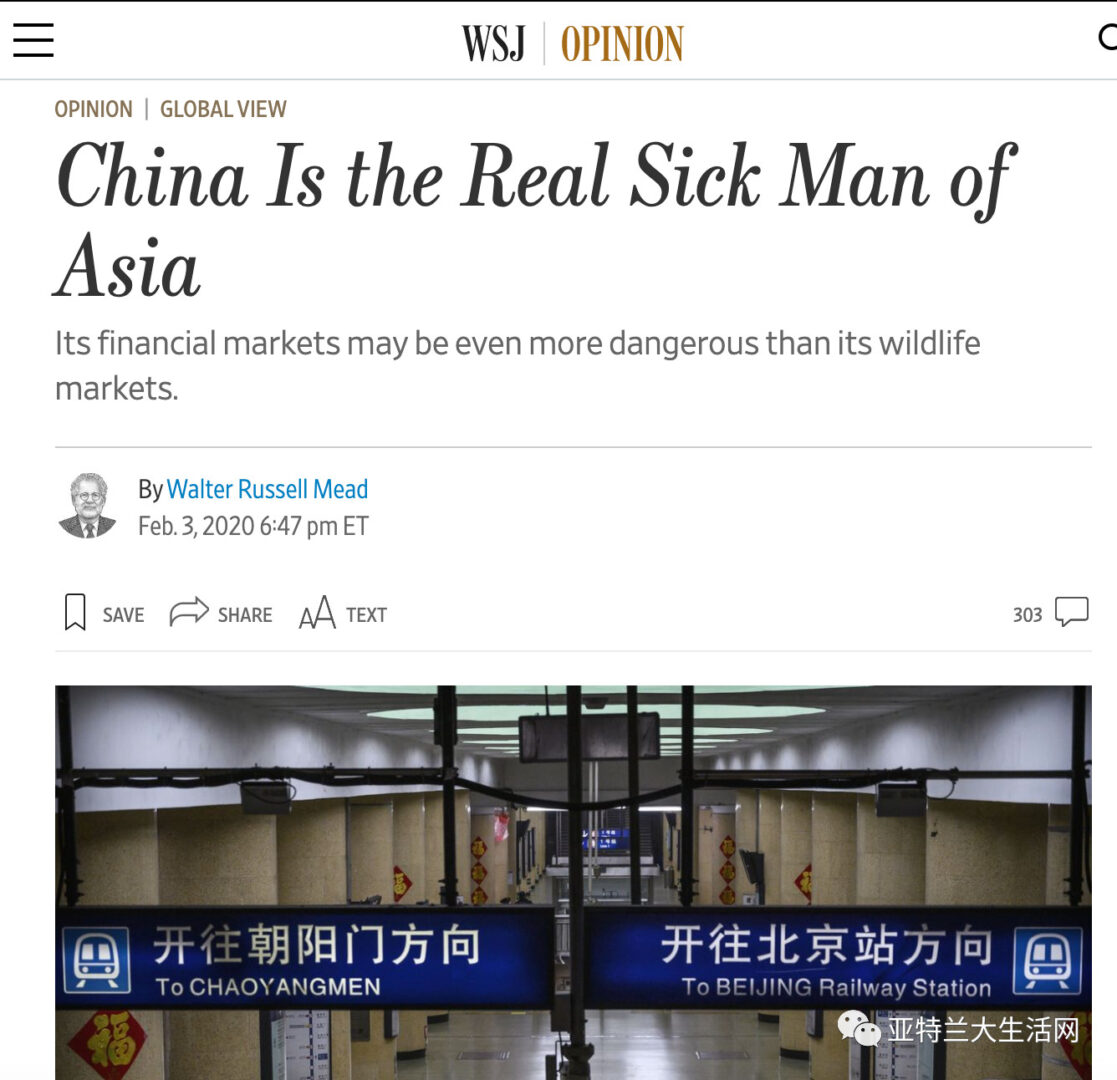
其实,如果说驱逐美国记者让川普不免窃喜的话,因为这个标题大动干戈就不仅太过玻璃心,也当真是贻笑天下了。
英文中并没有“东亚病夫”的说法,“Sick Man of Asia”也根本不是“东亚病夫”的意思,它是一个英文典故。“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落后国家的惯用词了。最早被形容为“Sick Man”的国家,是土耳其。19世纪中期,土耳其帝国国力衰败,屡被西方国家欺凌而无法振兴,因此被强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讥笑为“Sick Man of Europe”。此后,“Sick Man”一词,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
Sick Man从未特指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葡萄牙、法国、德国,乃至大不列颠帝国、美国都被称作过Sick Man。




外国人用“病夫”评价中国人,唯一见诸历史的是一位名叫李佳白的传教士,他在文章中将满清政府比做“病夫”,然后像医生一样开出“处方”,实际上对清政府的财政、教育和官员腐败提出的一些改革意见。
可见Sick Man从来都是用来批评政府,而从未辱骂国民。虽然,我个人觉得,中国人普遍体格不够强壮,被人高马大的老外视为“病夫”也并不奇怪。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歪果仁”反而常常夸奖中国人。比如:外国医生高登,在广州游玩时被轿夫抬着,他盛赞中国人的体力特别好;传教士医生德贞,夸奖中国人饮食节制、生活规律有序,比欧洲人更健康;欧洲医生也有针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条件,批评中国卫生条件差、造成天花流行,但他们反而称赞中国人在恶劣条件下能够生存,表现出强大的免疫能力。
实际上,“歪果仁”从来没有把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因为那样的话,就得说the sick men of Asia或the sick people of Asia,而这两种说法都不存在。
据学者考证,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不是外国人,却是中国人自己。1895年3月4日至9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题为《原强》的文章,认为:“今夫人之身,惰则窳[yǔ,瘦弱],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严复的意思是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病人,给这样一个病人治病,不能下猛药,只能调理、改良。
1896年10月17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的一篇文章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自此“东方病夫”一词广为流传,忧国忧民者常用它比喻自己的祖国。
“东亚病夫”最早出现于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1903年12月出版的梁启超所著《新大陆游记》,他在书中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东亚病夫”的说法由此传播开来。
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作品中出现“东亚病夫”的反省之声,并顺延到鸦片战争时期,将战争失败的羞辱与中国人鸦片烟鬼的形象联系起来,成为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结。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人跟人斗、民族跟民族斗,于是将国民身体和民族兴旺联系起来,“东亚病夫”就成为中国人为激发民族主义所作的自我污名化,就像小流氓打架打不过别人,就跟哥们儿说“他们骂我们是草包!”。
在李小龙时代,“东亚病夫”并非西方人和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称谓。虚构人物陈真,在电影《精武门》中里围绕“东亚病夫”匾额发生的故事,自然全是虚构。霍元甲虽确有其人,但在关于他的传说中,凡涉及“东亚病夫”的内容,也必定是虚构。
1956年,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中说:过去说中国是东亚病夫,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然后“五毛鼻祖”郭沫若写马屁诗,说道:“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
于是乎,“东亚病夫”成为不可跨越的红线,西方人批评政府的Sick Man,要是用到中国头上,那就是侮辱中国人,海外的小粉红就得上街游行、去白宫网站请愿。
至于中国是不是Sick Man,你我心里都有数。
《华尔街日报》文章中文翻译
源于“亚特兰大生活网”,深表感谢
这强大的中国统治者们本周一直都很烦恼,很明显是因为最近流行的蝙蝠带来的新冠状病毒。 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控制疫情并重新开始经济发展,但人们已经意识到,以前全世界都已经习惯了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但现在意识到没有任何事情,即便是伟大的北京力量,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新的冠状病毒将有多危险。 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仍在设法掩盖问题的真实范围,但在这一点上,该病毒似乎比埃博拉或SARS等疾病的病原体更具传染性,但致命性要低得多。不过,有专家认为 该冠状病毒与SARS具有同样的传染性。
中国对危机的最初反应并不尽人如意。 武汉市政府最初对病毒消息保持秘不外宣,中央有关部门后做出了积极回应,但目前看来效果也似不佳。中国的城市和工厂正在关闭; 而该病毒继续在传播。 我们可以希望当局能够成功地遏制这一流行病并治疗患者,但是迄今为止的表现已经动摇了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北京抱怨美国拒绝最近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非美国公民入境,这些投诉并不能掩盖一个现实,那就是,使这一流行病传播得尽可能快和如此之快的决定都是在武汉和北京做出的。
据分析师预计,新冠状病毒流行带来的最可能的经济后果,将是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短暂而急剧的下降,并随着疾病的消退而慢慢恢复。 最重要的长期结果似乎是加强全球公司“去中国化”其供应链的趋势。 在新的贸易战的威胁下,持续的公共卫生忧虑加剧了,供应链的多元化开始显得审慎。
各种新冠状病毒及其前身(例如SARS,埃博拉和MERS)流行传播的灾难事件,对我们的系统进行了测试,并迫使我们开始考虑那些不愿想象的问题: 如果存在像埃博拉这样致命的疾病,并且像新冠状病毒一样迅速传播的疾病,美国应如何应对? 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发生这种大灾难的可能性?
流行病毒也使我们开始思考地缘政治和经济假设学。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就是因为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将短暂被干扰的预期。 如果(也许是为应对流行病毒,但更可能是在大规模金融崩溃之后)中国的经济长期遭受甚至更慢的增长,将会发生什么? 这种事态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以及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如何?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可能比中国的野生动植物市场更加危险。 鉴于数十年来由国家主导的贷款的累积成本,地方官员与当地银行之间的纠纷,高耸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中国对于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调整来说已经足够迫在眉睫了。 即使是很小的初始冲击,也可能导致巨大的熊熊烈火篝火,因为所有虚假的价值,虚高的期望和资产分配不当都会爆炸。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监管机构和决策者是否具备将损害最小化的技术能力或政治权威,尤其是因为这将给那些与政治有联系的人的财富造成巨大损失。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甚至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但地缘政治和国际事务的学生(更不用说商业领袖和投资者)要记住,中国的实力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脆弱。 更具致命性的病毒或金融市场的蔓延可能随时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前景。
现在许多人担心新冠状病毒将在全球流行。 中国经济崩溃若发生,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将以同样的不可遏制的速度在全球蔓延。 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价格将暴跌,供应链将崩溃,世界各地几乎没有金融机构能够逃脱这种连锁反应。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复苏可能会很缓慢,社会和政治影响可能会非常严重。
如果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而缩水,给全球带来的后果可能也令人惊讶。 如果美国唯一可能的大国竞争对手退出了竞争游戏,人们就会担心可能的单极性状态会回归。 然而,在美国政治世界中,“孤立世界”,而不是“参与到世界”可能会突如其来。 如果中国的挑战逐渐消失,许多美国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可以安全地降低其对全球的承诺。
到目前为止,二十一世纪一直是黑天鹅时代。 从9/11到特朗普总统当选及英国脱欧,低概率,高影响力的事件重塑了世界秩序。 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在下一个黑天鹅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谁也不能说中国出现的新冠状病毒的流行就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