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中国文学的印象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果你觉得苏东坡的代表作是“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等词作,恭喜你:你中奖了!你在欣赏文学时,不知不觉被灌输了“五四史观”。
当然,你并不孤独。
在探讨文学作品的逻辑性与内在性、以及文学如何随时间而发展变化时,人们常常试图解释文学为何会从一个时期发展到另一个时期,例如为何中国文学从古典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
“五四史观”坚称白话文是文学发展的巅峰,而文言文、骈文等传统形式则被贬斥为“老旧”与“无意义”。胡适便是这种观点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所代表的“五四史观”至今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语文教育,仍然笼罩在这种“五四史观”之下,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学鉴赏与思考判断能力。
然而,这种看似进步的文学史观,实则隐藏着深刻的思维陷阱,不仅扭曲了我们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理解,还在无形中遮蔽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价值与复杂性。是时候揭示“五四史观”的局限性,并以更客观、多元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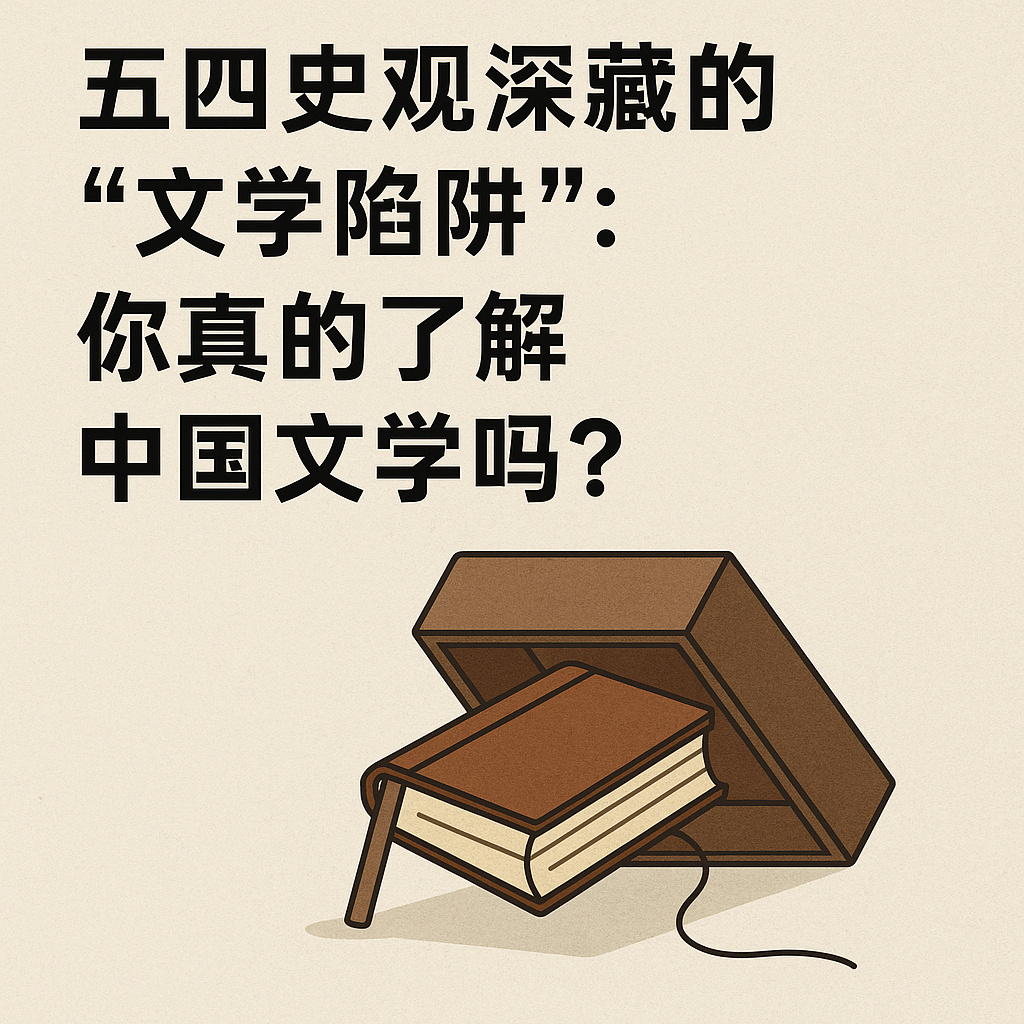
一、五四史观的内核:线性进步的迷思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思想风暴,也深刻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
“五四史观”的形成,受到了当时全球流行的主流思潮,以及中国“被长期殖民”的国际地位的影响。为了“富国强兵”等现实政治目的,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也倾向于顺应当时的需要。
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代表,五四文学史观体现了一种所谓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是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发展到今天的白话文,因此白话文是最进步、最革新的。而以前的文言文、骈文等是老旧、没有意义的文字游戏,是文人的自说自话。
这种“历史进化”与“线性进步”的意识形态,背后理论来自西方,即所谓的“演化观”。例如,英国学者斯宾塞的自然演化说认为,自然演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展法则,越晚出的就一定越好,即“后出转精”、“后来居上”。
将这种进步观将自然演化观应用于文学解释,就会形成所谓“线性进步意识”和“进步叙事”,认为文学是不断进步的,古代与现代之间是绝对化的单线进步过程,文学一定会朝着某种固定的方向、观念或目标发展,最终白话文一定会胜利,而撰写文学史的人,必然就会描述并证明这种文学精神开展的过程,以及如何克服阻碍,最终实现“平民胜利”、白话文最优秀的伟大目标。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认识。文学不应该是“文人游戏”或“精英自娱”,而应该由未经基本文学训练的大众投票决定?别再以通俗为标准,剥夺文学的深度与艺术性了!
二、文学史的“选择性失明”:谁被遗忘了?
五四运动全面否定传统,五四文学史观完全贬低传统文学,认为汉赋、骈文等形式艰涩、累赘、沉重,是普通人看不懂的精英分子的文字游戏,终将被淘汰。
于是,胡适批评杜甫的七律、尤其是《秋兴八首》是“诗谜”,因为别人看不懂,没有价值。但其实,在具备良好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看来,杜甫的七律空前绝后,是中国文字艺术登峰造极的杰作。
胡适赞扬韩愈的“作诗如作文”,认为这打破格律束缚,更加自由,符合“我手写我口”的最高文学境界。然而,美学大师朱光潜完全反对,他严厉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认为韩愈的做法是中国诗运衰落的关键。这才是学养深厚、不被政治影响的学者之洞见。
五四史观对文学史进行简单化的粗暴分期,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先秦(诗经、楚辞) -> 汉代(汉赋) -> 六朝(骈文) -> 唐诗 -> 宋词 -> 元曲 -> 明清小说”,用以证明文学向白话文进步。然而,这种“简单粗暴”不仅是武断的,更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宋词并非宋代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宋代诗作更加重要,词只是“诗余”。
五四文学史观会造成严重的“选择性失明”,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筛选和评价文学作品与作家,造成了文学史的片面性。这种史观倾向于以“忧国忧民”或“平民胜利”作为评判标准,导致对某些作家的误读。例如,白居易常被解读为“忧国忧民”的诗人,其《卖炭翁》《买花》等诗被视为杜甫“现实主义”的继承。但这种解读忽略了白居易作品的多样性与个人情感表达,过于强调社会功能,削弱了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
五四文学史观,就是用今人的视角去衡量过去的文学作品,这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判断问题。五四运动强烈的反传统思想,反应在文学史观上便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全面而整体性的反抗运动”,其中或许包含“庄严的救国用心”,却也是“昔不如今”的高举自我的错误思维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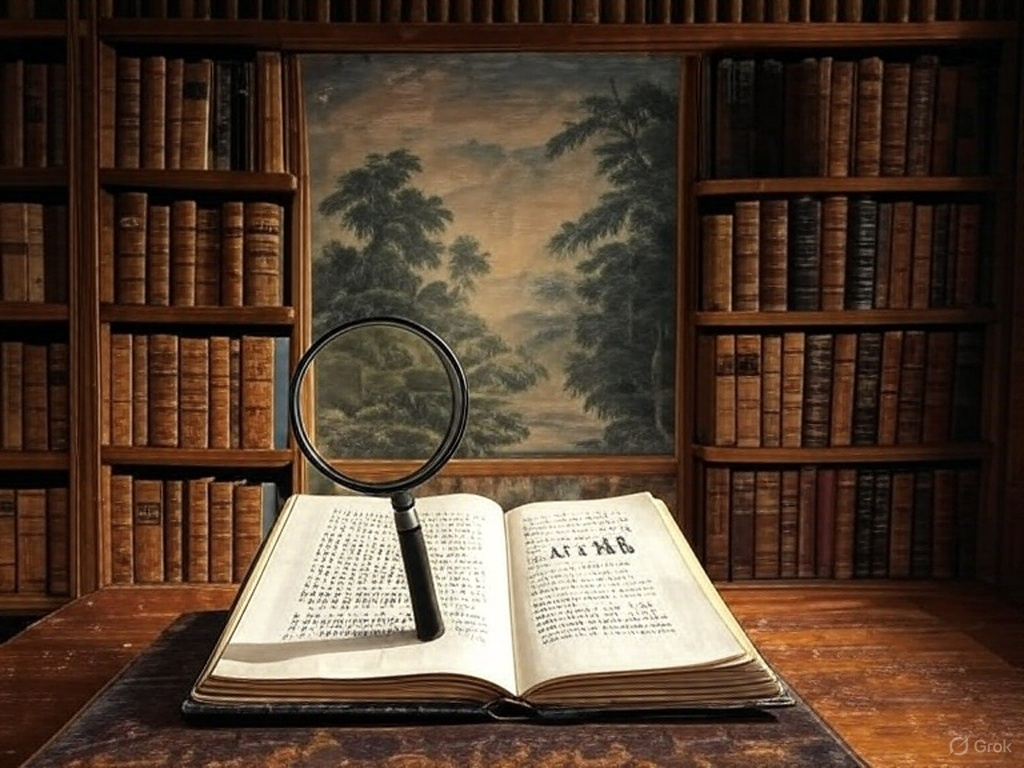
三、文学目的论的幻象:历史真的有“目标”吗?
在线性进步意识下,历史发展一定会朝向最终极、最有价值的目标进行。五四史观也为文学史赋予一种目的论,认为文学发展朝向某一固定目标前进,例如“人性觉醒”或“平民胜利”。
胡适等人将白话文视为文学的终极胜利,认为它打破了文人垄断文字的“特权”,实现了全民表达的理想。所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被解读为“情欲解放”、“个人觉醒”、“建立自我主体”的高峰,被歌颂为“至情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只要个人能够觉醒、独立自由、不受外在束缚,就是人的觉醒的最高境界和建立自我的方式。然而,这种解读是现代人将自身价值观投射到古代文学的结果,忽视了作品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的真实意图。
事实上,杜丽娘的故事确实充满浪漫色彩,但其精神内核更接近于明代士人对“情”与“理”辩证关系的探索,而非简单的“反礼教”。
同样地,曹雪芹并不认为《红楼梦》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其亲友圈更多将其视为集体记忆的情感抒发,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巅峰”。
五四史观的“目的论”强加了一个超越历史的目标,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偶然性与多样性。
四、跳出陷阱:重读与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
文学史需要不断地重读、重写,因为每个时代对过去文学的认识都不同。五四史观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再适合用来面对过去的文学。因此,我们需要重塑文学史,尽量避开盲点和干扰,摆脱历史包袱和意识形态,用新增加的知识体系、新时代应有的新视野,对过去文学做出更客观、更有意义的建构。
《剑桥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通过“历代读者的接受史”与文化研究的角度,摒弃任何单一史观的支配,力求还原文学现象的时代语境。这种方法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关注当时人对文学的理解与运用,而非以现代标准裁量。例如,苏东坡不仅是宋代最伟大的词人,他的诗、文、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的成就同样值得重视,而诗才是他的核心创作。又如,明清才女文化十分兴盛,反映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贡献,她们的作品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通过重读与重写,才能打破五四史观的线性叙事,呈现一个更加多元和立体的中国文学图景。
五、结语:以开放心态迎接文学的复杂性
五四史观虽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与文化革新,但其“线性进步”的迷思、“选择性失明”的偏见以及“目的论”的幻象,构成了理解中国文学的深层陷阱。
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就必须跳出这些陷阱,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正如杜甫名言“转益多师是汝师”,我们应广泛吸收不同视角,摒弃单一的意识形态,从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被误读或遗忘的文学传统,去理解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感受到它跨越千年的深邃魅力。
